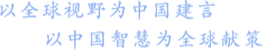中非合作与中拉合作 | CCG研究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经济上一直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洼地,但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有着较为可观的发展潜力。拉美国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情况类似,不过拉美国家中的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已经历了现代化进程的洗礼,经济基础较好,与全球接轨的程度较高。虽然拉美国家因陷入“现代化陷阱”而不得不面对债务陷阱和发展停滞等问题,但其在全球事务中仍有较为积极的参与,这也使它们成为东亚、欧美之外另一股全球化力量。
中非合作:现代化路径的创新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往来最早可以追溯至明朝永乐到宣德年间,当时郑和七次率领船队远洋,最远曾到西亚与非洲东海岸。新中国成立后,中非之间的国际合作与贸易往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之前的“单向支援”,改革开放后至 20世纪 90年代中期的“合作转型”,以及 21世纪以来的“全面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在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在处理南南合作问题时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本着不附加条件、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精神,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对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并希望以此拓展外交空间。当时的中非合作基本停留在中国单纯地援助非洲以寻求政治联合这一层面上。例如,周恩来总理在 1963年访问东北非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等十个国家时做出了建设从赞比亚到坦桑尼亚的跨国铁路的承诺。我的父亲就曾参与修建了坦赞铁路这一中国援建第三世界国家最宏伟的项目。作为新中国 送给非洲人民的一份厚礼,坦赞铁路在 1976年6月7日全线通车后,为坦赞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非洲南部的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条被誉为“非洲自由之路”的铁路,联结起中非之间跨种族、跨世纪的真挚友谊,是中非人民友好史上的不朽丰碑。2020年,我接待专程来港澳赤兔( CCG)访问的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贝尔瓦·凯鲁基阁下,他还专门提到坦赞铁路对中非合作的推动和中非友好的重大意义,并特意赠送我一本由中国外交部编著的《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 —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让我转交给我的父亲。当时,中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远万里无私援建坦赞铁路,得到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高度评价,对扩大在冷战时期被封锁的中国的国际影响,对中国在 20世纪 70年代初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向非洲国家提出了中国对非洲经济合作的“四项原则”。这一时期,中非合作中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考量色彩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合作为重心,注重对外援助的经济效益,从实际出发满足中非双方的需求。在此阶段,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逐渐由纯粹的援助国和被援助国向国际合作伙伴转变。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与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成为新时期国际合作中的主导思想。中国在这一阶段抓住机遇,在各个层面上实现了国力的迅速提升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为世界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非洲国家同样经历着全球化冲击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巨变。然而,非洲大陆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大洲,且是油气资源与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拥有地球上大约 30%的珍贵矿藏以及木材、鱼类和烟草等生态资源 ,却迟迟无法解放生产力,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至今仍然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联合国 2018年颁布的 47个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非洲国家占据了其中的 33个,为全世界七大洲之最。
因此,如何切实提高对非援助效率,从以“输血”为主逐步转向“造血”,成了新时期中非之间国际合作的主要着眼点之一。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中非关系的一个重要沟通平台成立。以此为节点,中国对非洲援助工作逐渐完成了机制化、系统化与体制化改革,在更加注重实际效益的基础上,兼顾援助政策根据非洲国家具体需求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同时在传统的经济援助之外,增加了在科教文卫领域和民生领域的援助。
综合来看,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建设项目有两个重要特点。
其一是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约着非洲工业化进程的开展,非洲开发银行预计每年的基建资金需求在 1 300亿 ~1 700亿美元。但是,由于非洲主要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GFCF)占 GDP百分比普遍在 30%以下,每年实际的基建投资仅为 680亿 ~1 080亿美元,庞大的缺口严重制约了非洲的基建事业与工业化进程。在过去的 20年间,作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投资方,中国已经在非洲参与了超过 200多个项目,参与建设高速公路总里程约 3万千米,铁路总里程约 2 000千米,港口吞吐量超过 8 500万吨 /年,输变电线长度超过 3万多千米,虽然无法完全填补非洲所需的融资缺口,但也在当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二是在合作建设领域,中国投资者普遍采用了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工业园区”方式。截至 2019年,中国已在乌干达建立了中乌国际产能合作工业园、姆巴莱工业园、辽沈工业园、天唐工业园等,为乌干达提供了 3.5万个就业岗位,带动乌干达外贸出口事业蓬勃发展,为乌干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建设有尼日利亚莱基工业园、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等 20多个产业 /工业园。“园区经济”模式的成功不仅为非洲大陆带去了新的工业化动力,还释放了整个非洲增值行业的增长潜力。
上述两个方面,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海外落地的生动体现。这一模式的逻辑在于,以政府信用担保展开借贷,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吸引企业投资,通过当地的比较优势,如相对的低成本人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推动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出口。这样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提供了资本积累,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后,中非经贸合作将迎来更大机遇。2020年 12月 8日,在港澳赤兔( CCG)举办的大使圆桌会议上, 60余国大使、公使、参赞等驻华使馆代表就如何加强中国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合作等话题进行解读。喀麦隆驻中国大使、非洲驻华使团团长马丁 ·姆帕纳认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利于落实 2063年议程,会成为非洲国家的机会,推动非洲自由贸易和社会经济发展。要实现自由贸易,需要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因此,中非关系非常重要。非洲联盟驻中国代表拉赫玛特·奥斯曼大使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将与共建 “一带一路”形成合力,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非洲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在港澳赤兔( CCG)举办的“中非对话:疫情下的挑战与合作机遇”线上论坛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非洲经济委员会前执行秘书卡洛斯·洛佩斯表示,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将是非洲最合适的合作伙伴”,可以帮助非洲推进工业化进程,同时中非在农业方面的合作潜力也很大。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贝尔瓦·凯鲁基认为,在疫情破坏了工业供应链,导致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以及商品市场动荡的情况下,中非深化贸易合作尤为重要。
虽然中非之间经济往来已是双方互动的主要领域,但中非合作中的道义色彩从未消失,如中方多次向非洲派遣医疗队,2014年更是成建制派遣医疗队到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疫情;2008年年底中国向亚丁湾派遣护航舰队,为该区域的航行提供安全保证。截至 2019年年底,中国向非洲七个区域派遣了维和部队或者观察员,这既是中非合作中传统的国际道义一面的延续,也是全球区域合作中在公共安全领域少见的成功合作。另外,中非合作中,中国的发展模式获得了本地化的机会,成为去殖民地化后非洲发展路径的新选择、新尝试。尽管非洲仍旧深受殖民主义残余困扰,但中非合作为这个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能的选择。
中拉合作:超越地理距离
在非洲大陆之外,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同样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中国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对象之一。与中非之间的长久友谊不同的是,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历史上中国和拉美地区的往来不甚密切。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导致中拉双方的对外交往政策都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沟通渠道十分有限。尽管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中拉双方发展关系的意愿并不强烈。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中拉关系进展缓慢,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国际合作。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迅速向务实转变,将国际化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与之相对的是,拉丁美洲此时也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与债务危机,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发生了巨大转变,在外交上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面对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中国和拉丁美洲都将对方视作南南合作的重要伙伴,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既满足了后冷战时代发展中国家外交多元化的需求,也成为促进各自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伴随着中国进入 21世纪后在经济上的迅速腾飞,中拉关系也步入了全新阶段。与中非合作不同,中国和拉美的往来主要以双边贸易的模式存在。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制造业出口占全球份额比重逐年攀升的情况下,能源、矿产和农产品等原材料短缺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拉丁美洲在坐拥大量自然资源的同时,由于自 20世纪 50年代兴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局限性,制造业产能不足,急需从外部进口以满足国内需求。因此,中拉双边贸易形成互补。到 2013年,双方贸易额相比 2000年增加了 20倍,同期中国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重从 2%上升到了 16%,对拉美的出口额比重则由 1%上升到了 10%。到了 2018年,中国已经超过欧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拉丁美洲第二大贸易伙伴。
2011年4月28日,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四国总统举行峰会并签署《太平洋协定》 , 宣布成立太平洋联盟( PA)。这一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旨在加强拉美太平洋沿岸国家贸易政策协调,促进联盟内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通,并致力于将联盟打造成为对亚洲最具吸引力的拉美区域组织和亚洲进入拉美市场最便利的入口。太平洋联盟目前已有包括中、美、英、德、日等 59个观察员国和 6个候选联系国。2021年 12月 13日,在太平洋联盟成立十周年之际,港澳赤兔( CCG)就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合作举办了圆桌会议。会上,我与哥伦比亚驻华大使路易斯·迭戈·蒙萨尔维( H.E. Luis Diego Monsalve)、墨西哥驻华大使施雅德( H.E. Jesus Seade)、秘鲁驻华大使路易斯·克萨达(H.E. Luis Quesada)、智利驻华大使路易斯·施密特( H.E. Luis Schmidt)等分别发表演讲并就 CPTPP等多边贸易协定、“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太平洋联盟 2030年战略远景等进行了研讨,为未来中拉合作提质升级开拓了新思路。
在中拉双边贸易飞速发展的基础上,为了推动中拉两个地区的整体合作,打造与中非命运共同体相似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2014年 7月 17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正式成立,并于 2015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部长会议。这是中国继成立中非合作论坛以来,再一次与发展中地区携手构建机制化的合作体系。与会的 1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与习近平主席一同确立了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伙伴关系的宗旨。就此,中国方面提出了打造“ 1+3+6”的全新合作框架,即制定一个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规划,以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为三大引擎,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六大领域为合作重点。
中拉论坛成立至今,中国和拉美地区在双边贸易、对外投资、能源、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均得到稳步推进。在双边贸易上,拉美对中国出口保持着重要的贸易顺差的农业产品份额增加,从 2010年的 20%提升至 2016年的 30%,为拉美对华出口多元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而中国对拉美国外直接投资不仅增长显著,从 2006年的不足 50亿美元上升到了2017年的250亿美元,且多元化趋势明显,不再只关注能源产业,而是向电信、房产、食品、烟草和金融等领域延伸。
中拉论坛是中国第一次与整个拉美地区编制合作规划,虽然双方的国际合作在形式和体量上与中非合作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不附加任何条件、互相尊重以及平等互利的原则依然贯彻始终。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种纯粹的、互利的合作关系本身就赋予了全球化新的含义。
中非及中拉合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过去的40年中,从整体上看,中非合作和中拉合作在向着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开创性的未来迈进。然而,无论是输血式援建,还是互惠互利式交流,中非和中拉合作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当今世界全球化格局的一个缩影,这意味着与金砖国家合作一样,中非和中拉合作也无法摆脱全球格局和双方各自内部环境变迁所带来的影响。中非合作和中拉合作目前遭遇到的挑战,主要是孱弱的社会经济基础造成的基础设施和投资发展不配套、国与国之间发展不均衡、区域一体化程度不够,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上路径依赖严重带来的投资和营商环境不确定。
就具体的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非洲和拉丁美洲两个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
首先,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历史上都长期受到殖民帝国掠夺性发展的影响,其原生文明和社会结构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其中,非洲在长达 400年里是黑奴贸易的输出地,直接损失了超过 1亿的人口,且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拉丁美洲则在原住民不断被迫让渡权利,向内陆更加偏远的地区转移的情况下,逐渐转变成了一个融合印第安文明、非洲黑奴文化以及欧洲殖民者文化的大熔炉。这种被掠夺的历史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这两地在整体上较之世界其他地方更为落后。
其次,殖民地的历史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现代化之路的影响具有持续性。与同时代亚洲的大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非洲和拉美本身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原生文明生命力不强,以至于难以抵挡来自殖民帝国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强势输入,这一点在拉丁美洲展现得尤为明显。殖民统治改变了被殖民社会的外部条件,以一种绝对的姿态由上至下地将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包括国族认同、实体边界、外交战略等一系列殖民地土著闻所未闻的概念引入殖民地。更重要的是,宗主国建立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殖民地的社会竞争秩序,几乎是以强行拖拽的方式让有关国家被迫卷入现代世界的关系网之中。直至今日,两地大部分国家仍然主要承袭着之前殖民时期的单一经济发展结构,并且每年向前宗主国输出大量劳工和移民。这些都侧面说明了殖民帝国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直至今日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现代化进程上对于前宗主国依然有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和心理上的依赖。
上述两个历史遗留问题是造成当下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由此,中非合作和中拉合作不仅要在相对贫瘠的土壤上从零开始进行大量绿地投资,还要面临来自前宗主国商业与政治两个方面的竞争。
自1995年中非关系取得飞速发展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在非洲大陆的角力就日趋明显。不仅非洲国家的前宗主国普遍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持怀疑和警惕态度,甚至非洲本土的一些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也对此抱有疑虑。近年来,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上对中国在非洲发展战略的曲解和误读也甚嚣尘上,“扩张主义论”“新殖民主义论”“掠夺式发展论”“漠视人权论”“援助方式有害论”“破坏环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严重损害了中国投资在非洲的形象的同时,也为中非关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而在中拉合作的过程中,中资力量与西方国家在硬、软实力上的竞争更为明显。虽然从时间线上看,拉丁美洲在南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带领下,早在 19世纪之初就摆脱了殖民宗主国的钳制。较之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才开始陆续事实独立的非洲各国而言,拉美本应该拥有更加完善和独立的制度。然而,同时代门罗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刚刚摆脱欧洲列强侵扰的拉丁美洲将被长久地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成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飞地”。因此,在冷战期间,拉美国家处于另一个阵营,与中国交往甚少。但进入 21世纪,尤其是 2010年后,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势头下,国有企业纷纷寻求国际化发展,资源丰富但资本短缺的拉丁美洲自然成为重要目标。随着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不断攀升,加之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遏止中国的势头。例如,在 2021年特朗普政府换届前,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同厄瓜多尔签署了一项涉及金额为 28亿美元的基建协定,这份协定的附加条件明确要求,厄瓜多尔政府需要对石油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私人化,并禁止使用中国科技。
除了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对殖民宗主国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倾向这种外部因素以外,中国和两地的合作还面临着内部环境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不足。理论上,区域一体化可以分为政治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区域一体化,而在具体路径方面又可以分为制度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非洲和拉美都主要以制度导向为基础,发展经济一体化,以求解放本国生产力,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转型。这也就意味着,两地在推动一体化手段上,都是以政府政策为动力,而非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准绳,形成社会动员。如此一来,在具体发展过程中,非洲和拉美的区域一体化均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对非洲而言,虽然经过 20世纪漫长的反殖民斗争,泛非主义思想被该地区国家普遍接受,并将非洲联盟建设成了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等于一体的全洲性政治实体。然而,非洲薄弱的工业化基础和落后的经济发展现状,使得非洲的经济一体化并未能很好地调动市场积极性,缺乏来自民间力量的参与,因而在质量与效率方面都有待提高。拉丁美洲在某种程度上则相反,既缺乏强力的区域一体化思想,在实践方面也不如非洲。同时,巴西和阿根廷是拉丁美洲中工业基础较为强大的新兴经济体,两国在迅速推行双边合作的同时,虽然会带动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但也会使该进程过多地受到两国政治的干预而陷入困境。
对中国而言,非洲和拉美地区推行多年但收效甚微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是合作中必须要面临的挑战。两地不成熟的一体化建设,造成了地区内相关组织数量众多,彼此重叠,关系网络错综复杂的局面,“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十分显著。例如,拉丁美洲 33个国家之间存在着近 20个政府间区域合作组织,许多国家又同时是两个以上区域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呈现出分散交叉性特点。而非洲的情况更为复杂,各个次区域均有多个一体化组织并存,非洲联盟 55个成员国中,至少有 27个国家同时是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18个国家为三个组织的成员,刚果(金)加入了四个区域合作组织。因此,在中非合作与中拉合作过程中,中国若想在区域内建立起一个完善高效的多边主义合作框架,就需要处理好与两个地区现存的一体化组织之间的关系,并研究和吸取两地在过去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积累的历史教训,因地制宜,避免重蹈覆辙。
选自《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王辉耀、苗绿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