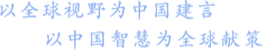陈志武:工业革命以来 人为造成的风险越来越突出
2022年5月9日
陈志武,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随着新冠疫情反复和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全球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 VUCA(乌卡)时代,我们如何应对各种“肥尾”风险,人类文明是否还能延续。知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近期出版了新书《文明的逻辑—人 类与风险的博弈》,并于近日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的专访,主 要讨论了人类文明与风险博弈的历史过程,以及在不确定的当下, 如何应对风险和危机。
1. 在西方进步主义的视角下,人类的文明程度通常分为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和启蒙五个阶段。在您新书《文明的逻辑》当中,您将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作为文明程度的主要坐标,是否意味着应对风险的工具越多,文明程度就越高?
陈志武:的确如此。人们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越强,避险的手段越发达,社会就会越文明,暴力发生的频率越低。在以往西方文献里,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比较大,关于文明程度的标准主要基于对于自然世界的掌握程度,也就是基于物质生产能力。工业革命让社会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发生的跳跃太大了 ,以至于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对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产生非常深的影响,并根据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理解程度、掌控程度来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文明的逻辑》里,我希望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步了、是否文明了,不只是基于生产率提升与否,而是必须看到,除了劳动生产率,也要看他们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是否提升。有的文明从两千多年前或者更早就开始,他们把注意力重点放在解决好生存安全的问题,也就是想法促进人们互通有无,分摊风险。如果一个社会花了很大力气改善了自己的风险应对力,即使没有能提升物质生产力,那同样是进步、促进了文明化发展。
比如儒家文明,孔子在论语里面讲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高度重视解决生存安全问题,重视风险挑战问题。在孔子和他后来的追随者看来,社会如果不把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安排好,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和风险分摊完全没有基础,那样,每个人一想到自己老了、生病了,就不会有安全感,一旦出现旱灾、水灾、地震、瘟疫等,就可能活不下去,或者被迫去偷抢,通过暴力甚至战争求生存。想象一下,人类如果历来只有“正常”状态,从来没有偏离“正常”的事件(即风险)发生,那么,人类就不会有苦难,也不会有暴力和战争;可是,自古至今,“不正常”时有发生,有气候的不正常,有生态环境的不正常(比如病毒瘟疫)或地震,也有人造的不正常,这些都会给人类生活带来“不正常”,带来苦难、暴力和战争。从这个意义讲,如何规避“不正常”即风险冲击,就成了催生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儒家几千年就是为了解决风险对生存的挑战而不断发展的,虽然儒家文明的创新并没提升劳动生产率。
2. 您书中提到“文明的对立面就是暴力”,而英国经济学家白芝浩曾说过,军事暴力可能也是一种文明。对此您怎么看,暴力的使用是否一定和文明的程度负相关?
陈志武:今天的世界要建立秩序,一方面要通过避险手段的创新降低违法犯罪和暴力的收益,另一方面还是要靠暴力增加犯罪与暴力的成本。但是,需要区分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这涉及到现代国家的概念,国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而私人及其组织,不管是黑帮还是个人,还是公司、宗族,如果使用暴力,除非是自卫,那就是非法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类早期为了降低暴力风险、提升人们应对战争风险的能力而发明了国家,以这种方式抬高非法暴力的成本,为社会中的个体提供公共品,从而使建立了国家的社会中的暴力发生率下降,文明秩序上升。在我的书里,以非正常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的高低来度量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以此将文明与野蛮暴力加以区分、对比。过去几千年,地球上,每年每10万个人死于战争的人数,从原来的六七百人左右下降到21世纪的不到0.3个人。有组织的战争暴力导致的死亡率在过去几千年下降了1500倍左右,而一般暴力死亡率也至少下降七百多倍。特别是在最近几个世纪里,这些文明化成就非常显著。
3. 在您的书中,迷信、婚姻、家庭、宗族、文化、宗教、商业等是您所谈“文明”创举的主要内涵,而非劳动生产率,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我本来是研究金融的人,金融工具应对风险的方式就是人际跨期交换,需要很多法律法治来保证金融契约能够执行。那么,在古代,没有正式法治,也没金融市场,但旱灾、水灾、地震、瘟疫等天灾人祸经常给人类带来“不正常”。大大挑战人类的生存;他们靠什么方式应对风险挑战呢?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首先,迷信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化进程中起到了安慰剂和建立规则秩序的作用。最早的人类如果没有迷信,就不会有规则和秩序,国家的起源实际上也是靠迷信。比如,我小时候在湖南农村长大,都是大人说“如果你不听话、乱来,将来雷公会打你”,就这样使我们变得守规矩、讲秩序,早期文明就这样出现;周公子建立的“天命论”大致也如此,说皇帝是守天命,老百姓都必须服从,至于皇帝是否真的是天派来的,没人能验证,但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及不同朝代的统治合法性就是这样靠迷信维护的。又如,在科学之前,深海打鱼的渔民如何应对台风等海上风险呢?他们如果不发明“妈祖”“天后”这些神、不在出海前举行迷信仪式,他们怎么有胆量去深海打鱼呢?
除了迷信的心理作用,主动规避风险挑战的创新也很多,甚至更多,从婚姻到家庭的发明,再到宗族的建立,这些都对人们应对风险的帮助更大,通过增强族人间的信任、让他们愿意共享资源并分摊风险,具体降低了未来没有东西吃的风险。况且,有了婚姻,就可以生小孩建立家庭,“养儿防老”等防范风险模式就有基础。儒家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规则发明,其本质就是使基于血缘网络建立的经济体制变得更加牢靠,或者说,儒家“孔家店”就是一套包括产权设置、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各方面的经济制度,而儒家伦理规则就是保障这套经济体制运行的规则。这些规则保证儿女对长辈回报、孝敬的责任,保证夫妻、兄弟、亲戚之间的跨期交换、风险互助关系能够被执行,而整个社会就是这样靠一个个宗族构成。
4. 金融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避险手段,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发展起来,西方国家发展出金融市场?
陈志武: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借贷金融在中国很早就有,比如《周礼》中的统治者在春天放贷,老百姓秋收时再还回来,利息一年20%左右;汉朝的《九章算术》里有好几个问题涉及借贷,问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所以说,中国社会的金融借贷业务在古代已经很普遍。
后来为什么没有发展金融市场?最大的原因是儒家选择基于血缘网络、也就是家庭和宗族来解决风险互助、资源共享的问题。从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的精英把重点放在强化血缘体系的文化创新上,最大化实现儒家的以德规避风险的体制安排,没心思发展金融市场所需要的外部“非人格化”法治制度。如,即使到18世纪的清朝,江西巡抚陈宏谋,在江西,后来在陕西、湖南等做了很多强化宗族凝聚力的创新。到晚清洋务运动需要发展金融市场时才发现,中国社会在超越血缘的非人格化的信任网络和相应的支持制度方面几乎是空白,所以,要发展证券市场、银行等,中国社会就完全没有制度基础。
即使到了今天,儒家文明影响越强、宗族越发达的地区,对于银行和证券公司的金融服务的需求还是越低,而那些宗族网络不发达的地区更能够接收外部金融市场提供的服务。
从全球来看,基于血缘的家庭和宗族、基于市场的金融和商业、基于教会的社会化组织、和基于政府权力的福利国家是四种不同的避险手段,这些手段虽然可以不同程度地帮助人类应对风险挑战,让人们的生活尽可能“正常”,但建立信任的方式各异,所需要的文化与制度内涵大为不同,这是《文明的逻辑》花大量篇幅所要阐明的地方。过去两千多年,自从轴心时代以来,各社会在这四种应对风险的方式中所做的选择各不一样,由此使各文明的特质也大为不同,这也是从风险角度审视文明背后的逻辑,能带来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认知。在人类历史上,这四种解决风险挑战的方式之间一直相互竞争排斥,尽管从道理上讲它们应该是彼此合作补充的。
儒家文明、希伯来文明、埃及文明,以及由希伯来文明延申出来的犹太教、基督教文明,这些基于农耕的文明起初都是排斥商业、排斥金融。孔子强调“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主张通过“义”规定谁对谁有分享责任、有回报责任,以“义”解决人际互助,而不是靠市场交易,亦即看谁出价高来互通有无。但基督教社会在中世纪后期特别是新教改革对这些观念做了调整,而儒家文明一直在坚守,直到洋务运动才改变一些。
5.当今世界仍然不太平,新冠疫情导致逆全球化、俄乌冲突让战争再次回到人类视野,这些“肥尾风险”是否会催生更多暴力?人类的发展是否仍然逃不出战争、和平的风险循环?您所说的工业革命后的三大工具箱——福利国家、货币国家、财政国家还能否发挥作用?如果不能,人类是否有新的工具箱?
陈志武:在工业革命之前,不管原始社会还是农耕社会,都要靠天吃饭,人类社会面对的风险挑战都是自然风险,如旱灾、水灾、地震、瘟疫。工业革命以来,人为造成的风险就越来越突出,从风险类别和性质上来看,工业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当下不管是战争,还是一般暴力都有所抬头,比如西方社会一些人对华人的攻击。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人类越来越走向文明、去暴力化,但肯定不是一条直线,短期里会有波动,“往前走三步,然后退两步”的事经常发生。但对未来,我还是很乐观。
如今我们面对同样的挑战。人的本性决定了有的人“不撞南墙不回头”,人类必须要经历一些遗憾和波折,甚至一些人被牺牲掉、遭遇很多苦难,才会唤醒人们做一些新的避险创举,包括规避暴力风险、战争风险的创新,为接下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进一步文明化发展迈出步伐。人类发展到今天,即使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逆全球化,但全球化在很多方面很难逆转,各个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捆绑在一起的程度非常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经历过的。
不过,未来5-10年,地缘政治风险、冷战风险可能是主要的大风险之一,地缘政治风险靠三驾马车这些工具箱——货币国家、财政国家、福利国家—-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这些工具只是对于解决本国的经济挑战有一些帮助,对本国的老百姓提供一点“安慰剂”,但不会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世界缺乏一个更加权威的国际机构,具有立法权、执法权的“世界政府”来维持国与国之间的秩序。没有这样的机构,地缘政治风险还会存在至少几十年。
6. 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您怎么看现在传统因素的避险价值。比如婚姻,现在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离婚率越来越高,是不是说婚姻的避险价值已经越来越低?
陈志武:是的。不过,完全把避险功能、利益交换功能从婚姻中拿掉,在未来很多年还很难,我更多是从比重变迁的角度来看,现在婚姻中的爱情比重感情比重越来越高了。小时候见过很多包办婚姻,没有一个让我觉得有感情基础,完全是因为大家都要养儿防老,出于利益的考虑,所以原来的婚姻没有爱情,只有利益。最近这些年,特别是在中国一线、二线城市,婚姻家庭关系里,感情的比重越来越高了,这很好。
现在规避风险的手段多了以后,对婚姻带来很大变革性转型。上个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18岁以上的成年人大概只有24%左右是单身生活,离婚率很低。今天,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在美国社会是单身,比例在过去四十几年翻了一倍多。现在通过别的方式都可以把未来风险解决得很好,这让婚姻和家庭更多地立足于感情,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发达国家把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对于靠养儿防老的社会来说是颠覆性的,同性婚姻怎么生子女呢?
7.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作者戴蒙德曾断言,农业的发明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在您看来,工业革命之前,风险催生了各农业文明。俄乌冲突和疫情让人们开始关注粮食安全,您如何看待未来的粮食安全风险?
陈志武:好多年之前,我就一直说粮食安全的风险。中国没有土地这方面优势,对中国和其他人口大国来说,真正要长期解决好粮食安全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接收一些世界规则,加入世界秩序,以这个方式让各个国家更多的和平相处。通过贸易让像巴西、美国、乌克兰、澳大利亚这些土地肥沃的国家提供粮食,中国没有土地优势,所以解决粮食风险问题,就是与其他国家共同建设好和维护好世界秩序,努力使跨国合作更加有效,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但是现在地缘战略风险非常大,这个时候,一定程度上把本国的农业重新建立恢复,是可以理解的一些举措。
8. 新冠疫情反复,中国第一季度平均工资的增幅放缓至6.6%,低于2021年底的9.6%,也低于疫情大流行前的8%至9%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也放缓至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人们越来越不敢去消费,疫情对哪些行业影响较为严重,对哪些行业有利的?中国经济的挑战是什么?
陈志武:过去两年半,旅游业受的打击最大,同时受到冲击的还有酒店、餐饮行业。我有两个亲戚都开餐馆,有一个亲戚前几天说做不下去了,越来越难,没有几个人出来吃饭,到处都是管控。所以跟消费有关的,人与人汇集场景有关的行业受打击是最大的。
奥密克戎疫情之前,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制造还一枝独秀,因为过去两年中国把疫情管控得很好,其他国家就需要中国制造业帮他们制造东西。但是随着乌克兰战争等地缘政治风险恶化,很多国家都被提醒不能够太过依赖进口,中国出口今后的挑战会非常大。
9.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在哪里?
陈志武:官员、老百姓和社会精英都要接受的一个现实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40年、50年甚至100年总是增长下去。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国家的经济规模会不可想象。
就像个人可以很有钱,但很遗憾一天就是三顿饭,夏天最多就穿两层衣,尽管可以买很多房子,但只住一套房,自然需求的约束让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总是快速增长。房地产行业早已供给过剩,出口制造很难进一步增长,基础设施让中国的土地被糟蹋很厉害。所以环视一下,可以做的越来越少了。
10. 有人说衡量文明的一个标准是并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对照顾好弱势群体。对此你怎么看?
陈志武: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另一个方面。2000年左右我到北京,住在华清家园周边,每次觉得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华清家园等小区的房子那么贵,但周边是贫民窟。当时我就想,有钱人自己住得豪华、过得奢侈,而傍边就是贫民窟,这让他们怎么日子过得舒服呢?好在这些年,对于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得关注和投入增加很多,贫民窟情况好转很多。通过一些社会保障,抬高人们的风险应对力,让大家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在文明化道路上迈进。
11. 在风险多变的当下,财富配置应该遵循怎样的逻辑?随着全球货币政策收紧,股票等权益类资产是否已不具备配置价值,如何看A股市场的发展?
陈志武:A股市场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问题很多,即使原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候,房地产非常火红时候,也没有多少股民赚到钱。如果未来经济发展瓶颈越来越紧,挑战越来越大,那么大家去想想,你作为A股的投资者能有多大机会赚钱呢?
房地产供给过剩,很多家庭只有一个独生子女,已经买了几套房子,今后怎么消化还是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一些保险很重要甚至更重要,比如退休养老保险、健康保险以及一些意外保险等。同时,国内国外最好都能有资产配置,比如美国股市。
原本大家都忙于赚钱,现在必须花时间和精力做好自己的理财投资安排,让原来赚到手的钱不要轻易送回去。未来投资的第一原则就是避险保值,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动不动就翻多少倍。在安全的基础之上能够有多少升值就争取多少升值,不要去追求翻多少倍的投资增值,未来一些年不太容易再有这种收益了。
12. 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变局,人们处在各种无助和焦虑的情绪之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现在全球化系统中新冠疫情导致人们越来越分裂,您觉得人类是否会更加分裂?
陈志武:我觉得短期内会更加分裂,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很难避免了。我从1986年以后一直在美国生活,过去5年半在香港生活。比如说中国人在美国面对的不安全感,这是之前的40年没有经历过的。不同的社会、群体、人种之间的莫名其妙的矛盾和仇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多。这种分裂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会有所加剧。
但长期看,我还是很乐观。因为人类都希望生活得更好、更安全,这跟肤色、人种、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的,是跨文化共通的。只要这种活得更好更安全的愿望继续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经过一段遭遇后,大家都会去反思,然后找到规避分裂风险的办法,重回文明化道路。所以,人类文明史不只是物质生产率催生的历史,也更是追求更高的风险应对力所催生的历史。
13. 对您个人来说,如何面对这种焦虑?
陈志武:我今年快60岁了,过去这些年已经做了很多风险安排,特别是利用各种保险产品和养老基金具。对任何个人,把自己的风险挑战、生存挑战首先解决好,然后才有基础、有心思去关注社会、国家和人类的走向。否则,自己成了社会的负担。
14.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犬儒主义成为新的代名词,比如许多年轻人选择“躺平”,对于应对风险,给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
陈志武:对年轻人来说,在这样的时期,应该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人力资本上做更多投资。能够花几年时间读书钻研做一些研究,包括学一些新的技术,比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也包括多些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现在赚钱的机会少,可以在自己的人力资本上多些投资,由此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前些年少很多。前些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创业,然后到美国、中国香港上市,一下就可以赚多少个亿,那时读书的机会成本很高;而现在,这种机会成本下降了很多,风险资本支持创业的意愿也下降很多,所以,这时读书做研究,让自己知识和技能上多提升,等过些年创业机会又多了,依然可以全力以赴去做那些赚钱致富的事情。
文章选自商业周刊,2022年5月9日